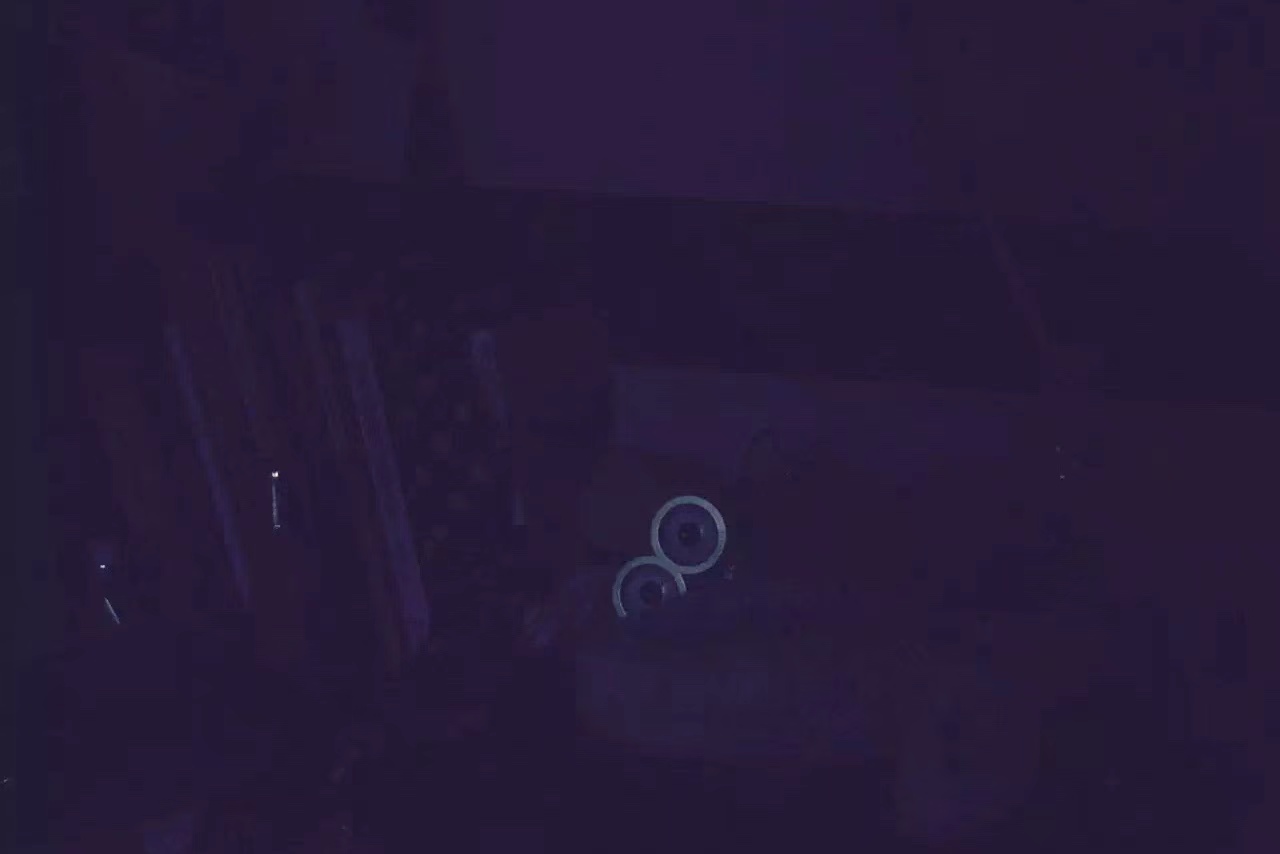陶梓二十五岁时,感觉自己已经病入膏肓。她以为她活不过那个冬天,她决定写一部小说,用小说来告别这个满是伤痕的世界。
陶梓在笔记本上写:等你完结,我就走。不贪恋这里的一方空气、一片蓝天......
深圳的冬天阳光明媚,陶梓的内心却冷若冰霜。她不知道向谁求救,不知道这些莫名而来的痛苦,是否可以讲给别人。
陶梓害怕,听到听她说话人,只是冷冷地回应一句,你想太多。
她只能用文字发泄痛苦… …
陶梓对文莘说,欧阳绛只爱爱情,沈绿然只爱青春。
那时,文莘已经在英国了,时差让她们的交流变得漫长。
很久之后,文莘回给陶梓的邮件里写道,她喜欢沈绿然这个名字,绿意盎然,充满生机。所以,不要让她过早离场。
陶梓看到文莘的邮件后,不争气地哭了。
那段时间,陶梓经常哭。没有原因,没有理由,走在街上,看着川流不息的车辆,阳光刺入她的眼睛,她的大脑里是一片空白,泪水却已经淌出眼角。陶梓想,或许这个世界上,只有文莘是懂她的... ...
文莘确实是懂陶梓的。她见过陶梓的母亲、见过武垣,听过陶梓说起程晗,也读过陶梓的第一部小说——《北锣鼓巷》。对于陶梓的经历,文莘不是旁听者,而是参与者。
文莘看着陶梓从清瘦变成消瘦,她相信陶梓每一次说不想活下去,都是发自真心的。可她什么也帮不了她,她只能听着她的痛苦,担心着某天听到关于陶梓的消息,是她的死讯。
锣鼓巷被车水马龙的鼓楼东大街一分为二。
南锣鼓巷喧闹,北锣鼓巷静谧。
故事发生在北锣鼓巷的一家叫做猫头鹰的小酒吧。故事的主人公,叫桃子。
夜幕降临,游客散去。南锣鼓巷恢复了安静,北锣鼓巷的缤纷才刚刚开始上演的。桃子坐在酒吧窗边,迷 幻的烟雾和酒瓶碰撞的声音,显得她格外孤独。酒吧老板注意她很久了,她总是一个人坐在窗边,望向远方。好像在等着谁的到来。
林木到酒吧时,桃子已经离开了。他们总是这样错过,一次又一次,未来可能还有无数次的擦肩。只是年少时,他们不懂得相遇的珍贵,只觉得错过就错过,还有下一次的相约,还有下一次的错过......
桃子离开酒吧,向北边走去,瘦弱的背影被幽深的胡同吞噬。桃子站在天桥上,看着飞驰而过的车,留下一片红色的光芒。她想,如果这时她跳下去了,谁会为她落泪?她的母亲吗?还是林木?
桃子坐上一辆无人的44路公交车,夜色中霓虹闪烁,繁华的街景仿佛自己不再悲伤。
16岁的桃子,活着的唯一希望,就是离开北京......
陶梓十八岁离开北京,二十二岁时回到北京。二十三岁时,又离开。她感觉自己已经没有再回去的理由了。活着的唯一希望,从离开北京变成了写完沈绿然与欧阳绛的故事。 年少时的陶梓也曾幻想,自己可以像韩寒一样年少成名。但那时她嫌弃自己文笔幼稚。
陶梓再看到稿纸上的《北锣鼓巷》时,清秀的字体、青涩的故事,陶梓觉得自己失去了少年的心,文字的表述变得不再唯美。
稿纸上的蓝黑色墨水,已经开始褪色。林木是谁?顾立吗?还是辛雨?或者是程晗?陶梓再也想不起林木的原型是谁,就如她想不起走在胡同里的心情是怎样的... ...
泛黄的日记本,被放置在书柜的角落里,很久未被翻阅。陶梓翻开日记,日记本里是陶梓潦草的字迹,几乎每一页纸张上,都有被泪水印染的褶皱:
11月15日 阴
看着你们一个个都开始有了自己的生活,我高兴着而又惶恐着。我害怕失去,当你们开始告诉我你和祂之间的故事时,我知道我们已经走远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倾听,然后走远。
或许有一天我写完我的小说,或者我妈妈离开了这世界,又或者看着你们都已经结婚生子。我习惯了做一颗弃子,我不会像松子一样苟活于世,我不会再期待明天可以变得美好。
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了,就把我能用的器官都捐了。我想只能请你们来参加我的葬礼了,来的时候给我带一支淡绿色的玫瑰,离开之后就当我们从未认识过。
12月1日 雨
我不想成为松子
但事实上,我没有松子坚强
我没有成为松子的资格
2月7日 雾霾
一个可怕的我来找我
不知道有朝一日我能不能摆脱那个可怕的我
她把我变得像一块生锈的铁
擦不出一点光泽
面对可怕的我
不管我心里怎么漠视、不在意她
最终我还是害怕她、讨厌她
... ...
春节,文莘回来了。他们三个照旧见面,陶梓和文莘喋喋不休地说着青春往事,辛雨安静地看着她们吵闹、大笑。他们玩起大冒险,辛雨输了,文莘让辛雨要蛋糕店小哥哥的联系方式,她们一直在笑。
陶梓感觉,她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笑了。她笑的脸僵了,眼角笑出了泪水,好像那段时间的悲愤,都随着笑声,离开了她的身体。
笑了很久,文莘把纸巾递给陶梓。陶梓听见文莘自言自语道,这样大喜大悲还是不太好... ...
回到深圳,陶梓决定去看医生。
医院候诊室,永远都是人头攒动。陶梓坐在候诊室,想就让他们挣吧、抢吧,她最后一个看。她坐在冰冷的不锈钢座椅上,看起书来。
一个陌生男人凑在她身边,露出满是牙垢的黄色牙齿,看着她傻笑。陶梓有些害怕,但又不敢表露,她知道在她周围的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无法自控的。她不知道她的惊慌是否会触及陌生男人脆弱的心,不知道他是否会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情。
陶梓的大脑一片空白,害怕的感觉充斥在她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内,她不敢径直离开,也不敢面露嫌弃,任由男人凑在她身边,叹着脑袋看她的书。
男人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他笑的像一个天真的孩童,可他看上去已经四十多岁了。
男人指着书上的单词,断断续续地对陶梓说:“这个怎么念?”
“Balance。”
“什么意思?”
男人不仅笑的像个孩童,说话的语气也很像孩童。
“平衡的意思。”
“巴冷思......平衡.......巴勒斯......平衡.......”
男人开始一遍又一遍的念单词,一个少年走到他身边,有些生气地说道:“行啊啦!冇烦人D!”
男人的头摆动的像只拨浪鼓,大声喊道:“不!念单词!我要学习!巴冷思......平衡......你念一遍!”
男孩儿无奈地看着陶梓,眼神中充满了抱歉。陶梓向男孩儿微笑示意。
“Balance,”男孩儿念了一遍单词,抓住男人让他离开。男人挣脱了男孩的手臂,对陶梓说:“他念得对吗?”
陶梓点点头,说:“他念得很好。”
男人继续问:“我的呢?巴冷思......”
陶梓继续笑着说:“你念的也很好。”
“巴冷思.......平衡.......巴雷斯.......平衡........”男人还在不停地念着,男孩儿无奈地坐在他身边,拿出作业开始写。一个女人从诊室冲出来,强行拽走男人。
男人被女人拖走后,男孩儿转过身对陶梓说:“真的很抱歉。”
“没事的,谁都不想的。”陶梓对男孩儿说。
“我真的很怕,怕有一天我也会这样......”男孩儿收起习题,向诊室方向走去。
诊室门口的人依然没有减少,陶梓从候诊室出来,站在树旁点了根烟。眼泪在她的眼眶中打转,她轻轻地抱住自己,心里说别怕。但陶梓依然很怕,她害怕有一天,她也会像那个男人一样,带给别人恐慌。她更害怕,如果真有那一天,她身边连一个替她道歉的人都没有。
陶梓问医生,她还要吃多久药。
医生说,大概两年。
陶梓说,她的检查报告并没有确认是神经问题。
医生说,你要听我的。
陶梓说,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比如去看一些相关书籍,或者转去做心理咨询。
医生说,你这是病,看书没用的。
陶梓说,到底是什么病呢?
医生不耐烦地喊着下一位,陶梓离开了诊室。
陶梓吃抗抑郁的药已经快半年了。这半年里,她除了每天在困顿中度过,偶尔不自觉的手抖,没有任何的变化。陶梓仔细看过药物说明书,有一些是治疗老年痴呆的,有一些是抗抑郁的,还有一个是安眠药。
每一次复诊,陶梓都会问医生,她到底是什么病?医生从没有正面回复过陶梓的问题,只是跟她说要相信医生。
陶梓想,她并没有不相信医生,她只是想要一个明确的答案。
走在回家的路上,阳光很好。陶梓却觉得很冷。她每一次去医院,都会想到第一次在医院时,遇到的那个男人。陶梓觉得男人可能有些强迫症,男人要一遍一遍的念单词,中间有人打断他,他会生气,会重新开始一遍一遍的念。后来陶梓见到“奇怪的人”越来越多,她开始觉得男人并不是很可怕,只是他的大脑无法平衡他的行为。
比起那些“奇怪的人”,陶梓觉得自己更可怕。她看起来那么正常,正常到可以一个人去看神经科;正常到可以控制自己恐惧的心情;正常到可以权衡面对男人时应该选择怎么样的态度,如果表露过激的行为是否会对自己的安危产生影响。她这么正常,却无法控制内心想要死去的念头。
陶梓甚至去咨询过保险经理人,询问他们哪些保险可以在自杀之后得到赔偿。陶梓想,如有有一日,她真的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或许是她唯一能给父母留下的。
冷漠的神经科医生,让陶梓有些怀念学校里的心理咨询师。
陶梓在学校里接受过心理辅导,每一次都是文莘陪着她。对于这件事,陶梓很感谢文莘。或许也是因为这件事,文莘才会经常担心陶梓真的会离开。高中毕业前,心理老师建议陶梓去医院看看,或许用药对陶梓来说会好的更快些。陶梓对老师说,她害怕吃药。她儿时被确认过癫痫,那时候没有人告诉她要吃多久药,她感觉是一辈子。她很害怕。
老师说,如果害怕也不必强求,或许陶梓到了新的环境,没有来自家庭的负担,一切变回自愈。如果情况变得不好,还是要找一个医生,积极配合治疗。 陶梓喜欢学校的心理咨询室,她对文莘说,在那里她能感受到心是在心里的,不是在嗓子里的... ...
大学生活,真的如老师所言,陶梓的心情变得平稳了许多。陶梓想,她是不是应该离开深圳?或许新的环境可以让她平静。
陶梓离开时,白雾去机场送她。
白雾是陶梓的大学同学。
或许陶梓不知道,除了文莘以外,白雾也很担心她,担心她突然的离开。这些年,陶梓和白雾住在一起,白雾还可以看着她。当陶梓说想要离开时,白雾的担心开始加剧,但她却找不到留下陶梓的理由。
托运完行李,白雾把陶梓送到安检口。
白雾对陶梓说,凡是别硬撑,心情不好就去看医生。呆烦了,就回来。
陶梓向白雾挥手,白雾转身离开。
陶梓到了新城市,心情变得稳定许多。工作越来越繁忙,她无暇再在意心情。只是那段时间,陶梓又开始做噩梦了。
陶梓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习惯了噩梦。
小学时,陶梓梦见班上的女生围成一个圈,她站在圈中间,所有人对着她扔羽毛,羽毛飞到她身前,变成了飞镖,她身上扎满了羽毛。陶梓觉得很痛,她看到自己遍体鳞伤,她放声大哭,却听不见哭泣的声音。陶梓从梦中惊醒,看到妈妈正坐在她身边哭泣。
因为那个梦,陶梓被确诊了癫痫。吃药吃到了初中毕业。停药之后,陶梓又恢复了做噩梦的习惯,只是她从未说过。比起噩梦,她更害怕每天被逼着吃那些白色的药片。好像每一片药都在讽刺她的精神有问题。
噩梦越来越严重,发梦的频率越来越高。陶梓总感觉有人在背后拍她。有时她甚至感觉到有双手,沿着她的脊骨,将她的后背撕开。每次惊醒,她都会想起自己满身羽毛的样子。
尽管陶梓内心抗拒,但理智一面告诉她,自己不能被噩梦吞噬,她决定再次去看神经科。医生怀疑陶梓儿时的病没有好,脑CT显示陶梓的大脑和常人有些区别。医生说,或许是先天不足导致了儿时的发病,也或许是儿时的发病影响了大脑的发育。总之,一切结果都是相互关联的。
陶梓开始配合的吃药。噩梦却越来越多。白天陶梓过得昏昏沉沉,她在药物的说明书上看到药品的副作用有行动迟缓、导致死亡的字样,她开始反感。每一次打开药瓶,陶梓都会想起小时候,那些圆的、扁的各种药片好像在警示着她,警示着她的不同,警示着她神经有病。
以前,陶梓感到悲伤时,会坐在房间里哭泣。悲伤随着泪水一同排出体外,她的内心变得平静。药吃了小半年后,陶梓不会哭了,但这并不是她不再悲伤。她感觉所有的悲伤,都因为药物的作用被压制在体内,她哭不出来,反而更加悲伤。
不仅悲伤无法发泄,陶梓的行动开始迟缓。早上她很难醒来,醒来之后感觉全身无力。上午坐在工位前,困得可以坐着睡着。上司问她是不是每晚都去蹦迪,不要玩的太疯影响工作。陶梓无法回答,她每天期待着午休到来。
午休的音乐一响,陶梓直接倒在工位上睡着,连午饭都不吃。有时陶梓能感受到有人在掐她的脖子。有时她感觉有人用塑料布把她缠在椅子上,一动也不能动。陶梓担心自己起不来,影响下午的工作,她奋力地挣扎,惊醒之后,却发现所有人都还在睡着。偶尔她还会感觉自己在磨牙,醒来之后问同事有没有听见她磨牙,同事说什么声音都没有。
陶梓挣扎了很久,最终决定自行断药。虽然她知道这样不对,但最坏的结果不过就是与世长辞,就算痛苦到要离开,她也想离开时,是清醒的、美丽的。陶梓不想药物吞噬掉她的神经,她不想变成一个目光呆滞、满脸傻笑的人。尽管她认为那些人仍有自己快乐的世界,但是她不想......
陶梓决定断药那天,她看一篇帖子。帖子是这样写的:如果你意志力足够强大,或许你会赢。但最好不要这么做。
断药后,陶梓的思维不再涣散。她不会再因为药物的作用,困到在办公桌前睡着,也不会因为每天打开药瓶而痛苦不堪。唯一的反应就是她会无法自控的手抖,抖的严重时,手机会从手上掉下来。手抖的日子大约持续了三个月,三个月后一切都恢复了平静。陶梓不再需要用酒精催眠,也不会突然的想哭。
陶梓想,或许她赢了... ...
十 七 岁,陶梓第一次走进学校的心理咨询室,在那里得到了片刻的安心。
十 八 岁,陶梓和母亲大吵一架,把高考志愿改到了深圳。
二十三岁,陶梓再一次离开北京,回到深圳
二十五岁,陶梓第一次自己去看神经科,再一次离开深圳
二十 六 岁,陶梓决定断药
文莘问陶梓,有过什么后悔的事吗?
陶梓说,应该没有吧。自从十 七 岁之后,每一个决定都是她自己做的... ...
《AFTER 17》
一步一步走过昨天我的孩子气
我的孩子气给我勇气
每天每天电视里贩卖新的玩具
我的玩具是我的秘密
自从那一天起我自己做决定
自从那一天起不轻易接受谁的邀请
自从那一天起听我说的道理
When I am after 17
一步一步走过昨天我的孩子气
孩子气保护我的身体
每天每天电视里贩卖新的玩具
我的玩具就是我自己
自从那一天起我自己做决定
自从那一天起不在意谁的否定
自从那一天起听我说的道理
When I am after 17
When I am after 1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