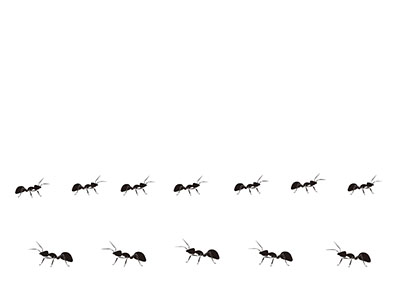参与小说的翻译工作如今已满一个月了,进度将近四分之一,我不禁有点雀跃,照这个趋势,也许四个月就能翻完,然后再用一个月修改校对,五个月就能结束。虽然这两周在其他的公司面试过两回都没有下文,有些失落,但前去这家小公司的路上,我的脚步就会轻快起来。果然是因为工作内容比较有意思吧。
这一天我像往常那样,出了地铁站后不紧不慢走去办公楼,不过今天与往常相比有所不同,路过的几栋楼都有人略有些兴奋地在窃窃私语。
没过多久我就知道这古怪的氛围是为什么了,有两辆警车停在某栋楼前面,围了一些看热闹的人,不知道是遭贼了,还是有人犯事被捕呢?
因为没有严格的考勤,所以我不慌不忙地凑近人群听了一会儿,原来是遭贼了。半夜有小偷潜入,被保安察觉,然后保安就倒了霉,被打倒在地,直到早上有人上班后才发现这桩事。救护车刚刚才载了保安离开,不知伤情如何,盗窃损失也还不知道。
到了工作室后,编辑也在。
“听说了吗?昨天晚上园区有贼光顾过。”
我点点头。这时艾克也进来了。
编辑让我们检查一下工作室的东西有没有被人碰过。公司资产没有损失,我们的私人物品也没问题,我们并没有多少私人物品放在这里,带来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值钱的。
“那就好。要是遭了贼,也是够讨厌的。”编辑准备回办公室,不过离开前她又回头说了句:
“对了,要是有人问起你们的工作内容,不要把具体的东西说出去。虽然是没多少获利空间的行业,但也是有竞争对手的。”
是那样吗?我觉得市面上有两种及以上的译本流通也是正常的,而且我们这还是已经有前辈译本的情况呢,我想不出有竞争对手又怎样,又不是什么高端科技。但我也没多说什么,就点点头。
目送编辑离开后,艾克笑笑说:
“大家有点紧张过头了呢。”
“邻家失窃,自家总归也会有些心慌。之后走的时候好好关上门窗吧,这里楼层低,有可能被人从窗里溜进来。”
艾克“嗯”了一声,然后我们休闲了几分钟,吃吃早点,聊聊来时遇上的骚动,之后就开始工作。
/***********************
第13章 自由民
是啊,每回一个人能感到满足的时间如此之短可真是奇怪。不过是一会会儿之前,当我还在骑马、还在受苦的时候,在这个涓涓小溪旁的隐蔽阴凉角落里所享有的这份和平、这一小憩、这一甜美的宁静看起来是多么像天堂,我可以在这地方不时灌一勺水到我的盔甲里,让我一直保持绝对的舒适;即便如此,我已经开始不满意了起来;部分是因为我不能点燃我的烟斗——虽然我很久前就开了一家火柴制造厂,我却忘了带上些——部分是因为我们没有东西可吃。这是另一个示例,显示了这个时代以及人们的那种孩子般的浅见。一个穿盔戴甲的男人在旅途中总是把他的食物寄托于运气,挂一篮子三明治在他长矛上的这个主意将会让他大受冒犯。比起被抓到在他的旗杆上挂着这么个东西,在整个圆桌联合里大概没有一位骑士不是宁愿自己死了。尽管没啥能比这样做更明智的了。我原本意图在我的头盔里夹带几个三明治,可是我行动时被打断,不得不找了个借口,把它们放到一边,然后一只狗叼走了它们。
夜晚逼近,连带着一场暴风雨随之而来。黑幕迅速降临。自然的,我们必须扎营。我在一块岩石下为那位少女找到一处不错的遮蔽处,之后离开去为我自己再找一处。但我不得已仍旧穿着我的盔甲,因为我自己脱不下它,又不可以让阿丽桑德帮忙,因为那看起来太像在大伙儿面前脱衣服。在现实中其实还不到那地步,因为我底下还有衣服;然而由一个人的教养所形成的成见是不会一下子就被去除的,我清楚,当要剥掉那件截尾铁衬裙的时候,我是会感到尴尬的。
天气随着暴风雨的到来而起了变化;风吹得越强、雨水在周边拍打得越凶狠,天就变得越来越冷。很快,各种各样的臭虫、蚂蚁、蠕虫之流开始离开潮湿处、成群拥来,爬进我的盔甲取暖;当它们中的一些表现良好、安安静静地依偎在我的衣服间时,大多数则是不安分、让人不舒服的类型,从不静下来呆着,而是不停地徘徊、追踪它们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东西;尤其是蚂蚁,它们以乏味的行列让人发痒地从我的一端走到另一端,一小时又一小时,是一种我再也不想一起睡的生物。这是我对处在这种状况下的人的建议,不要翻身或到处拍打,因为这样会激起所有不同种类的动物的兴趣,让它们每一个都想跑出来瞧瞧怎么回事,这让情况比之前还糟糕,当然也会让你厉声斥骂得更厉害,如果你办得到的话。尽管如此,如果一个人不翻身、不到处拍打的话,他会死;所以,或许这样做和那样做是一样的;没有真正的选择余地。即便在我冻僵了以后,我还是能区别出那股子瘙痒,就像一具尸体被加以电击疗法时一样。我说了这次旅行以后我再也不会穿盔甲了。
当我冻僵的同时又像在活生生的火里面,就像你会说的,是由于那一大群动来动去的爬虫,在所有那些难熬的小时里,那同一个不可解答的问题一直在我疲惫的脑袋里转啊转的:人们是怎么忍受这糟糕的盔甲的?他们是怎么办到一代又一代地忍受它的?他们忧惧着下一日的折磨时怎么能在晚上睡得着?
***********************/
艾莉:这一段写得倒是挺生动,但主人公竟然没想到带点驱虫药。
艾克:这也符合人设啊,主人公算工科人才。
艾莉:不,他能做火药,也学过治马,总该会点化学,虽然不知道效果,但制作火药、火柴时用到的硫磺可以用来驱虫。而且,他都不准备点露营装备。
艾克:那也符合幻想,哪个幻想小说里的骑士驮着大包小包去冒险呐?
艾莉:倒也不是没有,一般都会有个侍从、侍童之类的跑腿拿行李吧?
艾克:这么说来……不,《亚瑟王之死》里面,好多骑士就是像这里的主角那样,背后载着个有故事的姑娘就到处走。
艾莉:啊,这又是随着《亚瑟王之死》的风格吧,行。
/***********************
清晨终于到来时,我处在一个糟够了的苦况中:由于睡眠不足而无精打采、昏昏欲睡、累的要死;由于到处拍打而疲倦不堪,由于长时空腹而饥饿难耐;渴望着洗个澡,摆脱那些动物;还由于风湿而跛足。那么那位出身高贵者,带头衔的贵族,少女阿丽桑德·拉·卡特罗伊斯一夜下来怎么样了呢?哇哦,她像只松鼠一样神清气爽;她夜里睡得跟死人一样;至于说洗澡,大概她以及这片土地上的其他贵族都从来未有过,所以她是不怀念的。以现代标准来衡量,他们仅仅是略微改进的野蛮人,那帮子人呦。这位贵族小姐一点没有显示出对于吃早餐的急切——这同样有点野蛮人的味道。在他们的旅程上,那些不列颠人习惯于长时间空腹,知道怎么忍受;还知道出发前怎么在他们的船肚子里载满东西好对抗潜在的空腹,用那种印第安人和水蟒的方式。多半,桑迪装载了足够撑过三日徒刑的量。
我们在日出前就启程了,桑迪骑着马,我在后面跛行。半小时后我们碰上一组衣衫褴褛的可怜人,他们集合起来修理那个被看作是一条路的东西。他们对待我就像动物一般谦卑;当我提议同他们一起吃早餐时,我这异乎寻常的屈尊使得他们如此受宠若惊、如此不知所措,以至于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不能相信我是认真的。我的小姐扬起她轻蔑的嘴唇,而后撇到一边;她用他们听得到的声音说,她宁愿考虑和另外那群牛【注13-1】一起吃饭——这言论之所以让那些可怜鬼尴尬,仅仅是由于它谈及了他们,而不是由于它侮辱或冒犯了他们,因为它并没有。尽管他们不是奴隶,也不是牛群。以一个法律和措辞上的讽刺说法来算,他们是自由民。这国家七成的自由人口都是他们这个阶级地位:小户“独立”农民、手艺人等等;也即是说,他们是国民,真正的国家;他们就几乎是全部有用的、或值得拯救的、或真正值得尊敬的人,要是扣除掉他们就会是扣除掉这个国家,只留下一点渣滓、一些废物,有着国王、贵族和士绅的外形,无所事事、不事生产,熟悉的主要是浪费和破坏的技艺,在任何理性构筑的世界里都没有一点用处或是价值。然而,通过巧妙的设计,这个镀金的少数派不是待在它应属的行列尾端,却取而代之在行列的另一端昂首行进、旗帜飞扬;它把自己推选为国家,而这些数不胜数的沉默者已经允许这种事太久了,以至于他们最终把它当作真实来接受;不只是那样,还相信它是正确的、本就该如此。司祭们告诉他们的父辈和他们自己,这种讽刺的事态是上帝所安排的;于是,无人深思用讽刺来自娱自乐会是件多么不像上帝的事,尤其是这样劣质又一目了然的讽刺,他们就此放弃,恭敬地沉默下去。
***********************/
艾莉:桑迪的嘴还挺毒的呢。这里她说宁愿考虑和另外那群牛一起吃饭,原文是另外一群“cattle”,cattle,意义一是指牛群,意义二是指乌合之众。不过我没查到这个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意义二的。
艾克:但也没差吧,这词本身是就是13世纪才从别的语言转变过去的,6世纪的桑迪会提到这词真是个奇迹。
/***********************
这些温驯人们的谈话在一个原美国人的耳中听着有够怪的。他们是自由民,但他们不能离开他们领主或主教的领地,除非有他的许可;他们不能制作他们自己的面包,而必须在他的磨坊和他的烘房里磨碎他们的谷粒、烘烤他们的面包,还要为此大方付钱;不付给他一笔可观的收益分成,他们就不能卖出一块他们自己的地产,不给他送钱获得特许,也不能去买一块其他人的;他们不得不无偿地替他收割他的谷物,并且准备着一通知就马上去,任他们自己的作物在凶险的暴风雨中毁灭;他们不得不让他在他们的田地里栽种果树,之后,当他那些不留心的果实采集员踩伤了树周边的谷物,他们得把不平压在心里;在他的狩猎队策马奔过他们的田地、破坏了他们耐心苦干的成果时,他们不得不忍住他们的怒火;他们不被允许饲养自己的鸽子,当自大人的鸽舍飞出的鸟群落在他们的农作物上时,他们一定不能发起脾气杀死一只鸟,因为处罚会很糟糕;最终集得收成时,强盗们列队而来以征收之名敲诈勒索:首先教会拉走了其中十分之一的油水,接着国王的官员拿走了他那二十分之一,然后大人那儿的人对剩下的大举进攻;经历过那些后,被剥了皮的自由民有了将残余部分贮藏到他的谷仓里的自由权,以防那点东西还有去费事的价值;征税,征税,征税,征更多税,再征税,仍有其他税要征收——向这个自由又独立的贫民征收,但不会向他的那位男爵大人或那位主教大人征收,不会向挥霍的贵族或贪得无厌的教会征收;如果那位男爵要睡得安稳,那自由民必须在他一天的工作后熬上一整夜,抽打池塘好让青蛙保持安静;如果那自由民的女儿——不,君主政体最后的恶行是不宜刊印的;最后,如果那自由民在煎熬中变得绝望,发现在那样的条件下他的人生难以忍受,为寻求怜悯和庇护而献出生命逃向死亡,那么慈爱的教会就判处他身受永恒之火,慈爱的法律在午夜把他埋葬在十字街头,连带着一根穿透他后背的桩子,而他的那位男爵大人或那位主教大人将他所有财产充公,把他的寡妇和他的孤儿扫地出门。
这儿的这些自由民一大早集合起来修他们的那位主教大人的路,每人干三天——无偿的;每个家庭的当家,每个家庭的儿子,每人三天,无偿的,他们的仆人再增加一天左右。哇哦,就像是在阅览法国和法国人的故事,在那永恒难忘且受祝福的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故事,那大革命以一波——就一波——迅疾的鲜血海啸扫除了那种延续了千年的恶行:一次对那笔陈旧债务的清偿,用的比例是每半滴血抵债务中的一桶,每桶血都是在缓慢的折磨中从那人民身上压榨出来,就在那令人疲惫绵延十个世纪的时间里,那时间满是错误、羞耻和不幸,能与之比肩的唯有地狱。如果我们记得并探讨的话,发生了两次“恐怖统治”;一次是在激情中制造谋杀,另一次则是在冷血无情中;一次持续了不过几个月,另一次已经持续了一千年;一次将死亡强加给了一万人,另一次则是一亿人;但是我们的战栗都给了那一较小的恐怖统治所干下的“可怕之举”,可以这么说,那一片刻的恐怖统治;然而,相较于在延续终生的饥饿、寒冷、侮辱、虐待和心碎中死去,用斧子完成的迅速死亡是有什么可怕了?火刑柱之上于慢火中的死亡与闪电般的迅速死亡相较又是如何?我们所有人被勤勉教导要为之颤抖、为之哀悼的简短恐怖统治所填充的棺材,一座城市公墓就能容纳;但是整个法国都几乎容纳不下被那老得多又真实的恐怖统治所填充的棺材——那次不可言说的辛酸且可怕的恐怖统治,我们中没有人曾被教导过要去细看它的浩瀚或去施予它应得的怜悯。
***********************/
艾莉:我说,你学过编程吗?
艾克:没有啊,怎么了?
艾莉:吐温这人还真爱用长句子。法国大革命这儿我翻得好累,就是“一次对那笔陈旧债务的清偿……唯有地狱”这句。
艾克:确实,原句好长,逗号都没一个。但跟编程什么关系?
艾莉:以前,我觉得写得好的程序读起来就像文章一样。
艾克:咦?像文章?
艾莉:是说写得好的,面向对象的那种,变量名、函数名等都起得直观易懂的那种,格式整齐、注释到位的那种。
艾克:哦,我哪天也找几段看看。那现在呢?
艾莉:现在啊,我发现某些小说读起来……像是在读程序——没错,指的就是这篇。
艾克:难道你是想说,这段写得很难懂?
艾莉:不,好懂的,思路清晰,表达简洁,但翻起来反而麻烦,就像高级编程语言表达起来是很简洁,但如果用文字去解释的话,得写一大坨。这么一想,英语专业的去做编程大概也挺合适的。
艾克:我哪天问问英语专业的同学。
艾莉:你别真去问啊,就是我个人被长句折磨过之后的突发奇想。
艾克:我也就是开开玩笑嘛。
艾莉:这种长句翻起来达不到和原文一样的效果,句式完全不一样,只能说,建议有英语基础的读者不妨看看原文,这种一气呵成的长句念起来的感情基调比起我加了逗号的译文要更加强烈点,要同样翻成不带逗号的版本也是可以,但看起来累,效果也好不到哪里去。“ a settlement of that hoary debt in the proportion of half a drop of blood for each hogshead of it that had been pressed by slow tortures out of that people in the weary stretch of ten centuries of wrong and shame and misery the like of which was not to be mated but in hell. ”
/***********************
正和我分享他们的早餐并同我交流的这些可怜的表面上的自由民,他们对他们的国王、教会、和贵族满是谦卑的崇敬,就如他们最糟糕的敌人所欲求的那样。关于这点,有件事荒唐到可怜。我问他们,是否能设想曾经存在一国民众,他们,每个男人手中都有一张自由的选票,会去推选让某一个家族以及它的后代,不论是有才华的还是大傻瓜,排除了其他所有家族——包括选民自己的——而永远统治这个国家;还会同样去推选让特定的百来个家族拥有让人眩晕的顶峰地位,并冠以令人不悦的、可世代传承的荣誉和特权,除开这国家其余的家族——包括他自己的。
他们看起来全都莫名其妙,说他们不清楚;他们此前从没有想过这事,他们从来没想到过一个国家可以是这样的状况,竟然每个男人都能在政事上有发言权。我说我看到过一个——并且它会延续下去直到它拥有一个国定的教会【注13-2】。再一次,他们全部莫名其妙——在起初的时候。但是不久一个男人抬起头,请我再陈述一遍那个主张;并且要陈述得慢一点,那样能让他理解通透。我照做了;不一会儿他有了想法,一拳挥下,说他不相信一个人人有投票权的国家会以任何方式自愿地倒在泥巴和污秽中;还有,从一个国家偷走它的意志和选择权一定是种犯罪,并且是百罪之首。我对着自己说:
“这一个才称得上是人。如果有足够多的这类人在我背后支持,我会为了这个国家的福祉而一举出击,在它的政府系统里做出良好的改变,以此试着证明我自己是它最忠诚的公民。”
***********************/
艾克:这里又是个考验读者英国史是不是扎实的地方。
艾莉:我的英国史不太扎实,帮我解释解释。
艾克:主人公这些话是影射了英国历史,公元5世纪初,罗马人因西罗马帝国的衰败撤出不列颠之后,英国进入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从氏族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在氏族社会时期,氏族首领是公选的,被罗马人抛下的不列颠人依过往氏族划分推选出了领导者,形成许多王国,抵御日耳曼部族的入侵,亚瑟王传说起源自这一时期。传说中亚瑟王带领不列颠人赶走了入侵者,实际则相反,公元6世纪战胜不列颠人的日耳曼部族在不列颠建立了数个国家,然后在罗马传教士的影响下开始基督教化。基督教会在西欧封建化过程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是迅速封建化的催化剂,5至11世纪是教会力量全面发展的时期,教会利用自己的组织系统谴责民众的反抗、支持维护封建贵族和封建制度,使王权神化。
艾莉:原来如此,人类社会真是奇妙,从普选演变为专制,然后又花大把力气推翻专制,举起民主大旗。话说,以文中的背景,那时候距离罗马人撤出英国也仅仅过了一百多年,自由民们却都把王权认作天理了。
艾克:虽然相对人类历史而言,一百年就只是短短一瞬间,但人类社会却可以在短短二三十年里变得翻天覆地。
艾莉:没错,小时候到了夏天就在冰箱里堆满两、三块钱的雪糕是常态操作,如今……我在想今年能不能成功戒掉雪糕瘾。
艾克:虽说这几年的涨幅确实过分了点,然而,如果找到的工作能有平均工资水准,也不至于吃不起啊。
艾莉:吃不吃得起是一回事,能不能接受这个物价水准,又是另一回事了。
艾克:嗯……其实便宜的品类还是有的,只不过大城市的批发商不进货。
艾莉:是啊,之前跑到城郊居然还能看到不到一块的棒冰,我惊呆了……继续工作啦,跑题跑远了。
/***********************
你瞧,我的忠诚是那种对着自己国家的忠诚,不是对着它的制度或它的执政者。国家才是真实的东西,实质性的东西,永恒的东西;它才是那个要去照看、要去关心、要去忠诚的东西;制度是外在的,它们仅是它的衣服,而衣服会穿坏,变得破烂,不再舒适,不再保护身体免于寒冬、疾病和死亡。对着破布忠诚,为着破布呼喊,崇敬破布,为破布而死——这是种缺乏理性的忠诚,纯粹是动物性的;它属于君主制,是被君主制发明出来的;让君主制留着它吧。我来自康涅狄格州,那里的宪法声明“一切政治权力都是人民固有的,所有的自由政府都是基于他们的权威、为他们的利益而建立;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有不可否认、不可剥夺的权利以他们认为合宜的方式去改变他们的政府的形态。”
在那信条之下,一个公民要是认为自己看到那个州的政治外衣穿破了,却自保安逸而不去为一件新的外衣而鼓动的话,他就是不忠诚的;他就是个叛徒。就算他可能是唯一一个觉得自己看到了这个破败的人,也不成原谅他的理由;不管怎样,去鼓动是他的责任,而其他人的责任是,如果他们没有像他一样看到什么问题,那就投票否决他。
如今我在这里,在这样一个国家,总人口中每千人里只有六人有权利能说该怎么治理这个国家。那九百九十四人要是对统治体系表露出不满并提出去改变它,将会使那六个人一致哆嗦起来,那会是多么不忠,多么可耻,如此令人厌恶的肮脏反叛。打个比方说,我成了一家公司的股东,在那里,成员中的九百九十四人提供全部的钱并干了所有的活,而其他六人推选他们自己为永久董事会,然后拿走所有红利。在我看来,那九百九十四个易受骗的人所需要的是一次新的发牌。最符合我天性中狂放不羁一面的事情就是辞去“老板”那活儿,然后发起一场暴动,接着把它变成一场革命;但是我知道像杰克·凯德(Jack Cade)【注13-3】和瓦特·泰勒(Wat Tyler)【注13-4】这样没有先把他的素材们教育到革命水准就尝试那种事的人,几乎肯定会失败。我从来不熟悉失败,即便我本人确实把这词说了出来。因此,那个在我脑中有了一段时间、正在成型的“发牌”和凯德-泰勒那种的是相当不同的模式。
***********************/
艾莉:历史小知识时刻,有请艾克小哥哥~
艾克:你……行,嗯哼,杰克·凯德(Jack Cade),1450年英国亨利六世时期发生的农民起义的领导者,起义失败。
艾莉:瓦特·泰勒呢?
艾克:瓦特·泰勒(Wat Tyler),是瓦特·泰勒农民起义的领袖,1381年理查二世时期爆发的这场起义是英格兰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众暴动,以失败告终。
艾莉:感谢艾克小哥哥的精彩表现,现在继续下文!
/***********************
所以我没有跟那个待在那里和那群被虐待、被误导的人类羊群坐在一起大嚼黑面包的男人谈论流血和暴动,而是把他带到一边,对他谈了另一种事情。在我谈好之后,我让他从他的静脉中借了一点墨水给我;用这墨水和一块碎片,我在一片树皮上写下——
把他放进人类制造厂——
然后交给他,说:
“把它带去卡米洛特的宫殿,交到艾米亚斯·勒·波利特(Amyas lé Poulet)的手中,我管他叫克拉伦斯,他会明白的。”
***********************/
艾莉:不容易啊,这里首次出现了克拉伦斯的真名。
艾克:《亚瑟王之死》里面没有这名字,16世纪倒是有个叫Sir Amias Paulet的,当过苏格兰女王玛丽的狱卒,你觉得有关系吗?
艾莉:看不出有什么联系。
/***********************
“他是一个司祭,那么,”那男人说,热情的一部分从他脸上褪去。
“怎么——一个司祭?我不是告诉过你没什么教会的奴才、没什么教皇或主教的奴隶能进入我的人类制造厂吗?我不是告诉过你,除非你的宗教信仰不管是哪种都是出于自己的自由选择,否则你就不能进入?”
“圣母啊,却是如此,对于那我很高兴;因此听到这个司祭在那里,让我欢喜不得,生出寒心疑问来。”
“但是我告诉你,他不是一个司祭。”
那男人看起来离满意远着呢。他说:
“他不是一个司祭,却可以读?”
“他不是一个司祭却可以读——是的,说到那点,还能写呢。我亲自教给他的。”那男人的脸开朗起来。“而且这是第一件你——你本人会在那家制造厂里被教授的东西——”
“我?为着知晓那门技艺,我会把我心内之血都献出。哇哦,我会做你之奴隶、你之——”
“不,你不会的,你不会做任何人的奴隶。带上你的家人然后去吧。你的那位主教大人将会把你的小小财产充公,但没什么大不了。克拉伦斯会好好弥补你。”
***********************/
艾克:怎么样,你给这个章节配了什么图?
艾莉:这一章啊,我对小蚂蚁印象深刻,所以画了两排蚂蚁。
艾克:嗯……做人要诚实啊,你这是画了一只蚂蚁,然后复制粘贴吧?
艾莉:哎嘿~你别漏了,还有镜像呢~